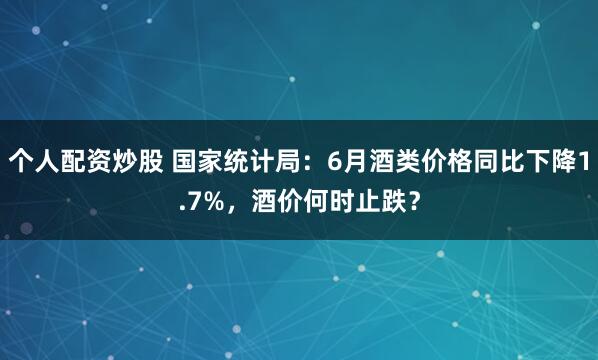19世纪末期,中国在朝鲜汉城取得的军事胜利,犹如一剂强心针注入了清廷士大夫们的血脉。这场被称为第一次朝鲜之乱的冲突中,清军成功挫败了日本的挑衅,这一胜利让朝堂上下弥漫着一种危险的乐观情绪。许多官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,却未曾意识到这种情绪正悄然演变成致命的轻敌心态。更令人忧虑的是,他们不仅浑然不觉,反而坚信自己的判断绝对正确。在这场胜利的余晖中,两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将领——张謇和袁世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:趁此良机将朝鲜彻底纳入中国版图,实行内地化管理。他们认为,这样既能加强对朝鲜的控制,又能将其打造为抵御日本侵略的前哨阵地。然而个人配资炒股,这还不是最激进的主张。以张佩纶、邓承修为代表的清流派官员,提出了更为惊人的方案:在山东烟台设立陆海军大本营,集结全国海陆兵力,直接对日本宣战,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东方邻国的威胁。那么,作为当时清廷实际掌舵人的李鸿章,对此究竟持何种态度呢?
张佩纶作为晚清流派的代表人物,与邓承修并称清末政坛双璧。所谓清流,是指那些将个人名节置于国家实际利益之上的官员群体。每当国家面临重大决策时,他们总是喊出最响亮的口号,却鲜少付诸实际行动。这类人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,常常让那些真正做实事的官员感到愤懑。然而讽刺的是,清廷却刻意保留着这样一批人。这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考量:为了防止知识分子像明末那样结社反抗,朝廷特意为这些科举出身的进士们安排了优渥的闲职。这些职位既不需要经世致用的才能,又能享受丰厚的俸禄,本质上就是国家豢养的一群政治装饰品。
展开剩余75%张佩纶的政治主张始终如一地强硬。在他眼中,任何妥协退让都是不可接受的耻辱。然而可悲的是,这位高谈阔论的官员对国际局势和现代外交几乎一窍不通,仍然固守着天朝上国的陈旧观念,用传统的朝贡体系来理解复杂的国际关系。中法战争期间,李鸿章特意安排这位主战派亲临前线,想让他将理论付诸实践。结果当福建水师稍遇挫折时,张佩纶竟成为第一个临阵脱逃的官员,直接导致左宗棠苦心经营数十年的福建船政厂毁于一旦。
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中法战争的惨痛教训并未让张佩纶有所收敛。短短数年后,当朝鲜局势再度紧张时,他又开始高谈阔论。这次,他与邓承修联名主张立即对日宣战。他们的理由是:既然张謇、袁世凯这样的年轻将领都能轻松平定朝鲜乱局,击败日本使馆驻军,那么日本显然不堪一击。他们鼓吹中国应该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东征日本良机,一举消灭这个潜在的东亚威胁。那么,张佩纶的具体论据是什么?这些主张又是否具有可行性呢?
张佩纶自称长期关注日本明治维新。在他看来,日本民众普遍厌恶新政,渴望恢复幕府时代的闭关锁国政策。他还指出,日本萨摩藩与长州藩的权力斗争导致国债高筑,纸币信用崩溃。虽然日本在军事改革上效仿西方,但只是徒有其表,既缺乏名将统帅,又缺少老成谋国的重臣。关于日本海军,他认为除了旗舰扶桑号尚可称道外,其余多为木铁混合结构的陈旧舰只,根本不值一提。陆军方面,他估算总兵力约五万,海军仅四千人,且吃空饷现象严重,不得不招募浪人充数。这样一支缺乏实战经验的军队,与中国精锐的湘军、淮军相比,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
平心而论,张佩纶的论述并非全无根据,他确实做了一些调查工作。但令人深思的是,他所指出的日本种种弊端,当时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?
邓承修作为广东惠阳人,年仅二十岁就在咸丰年间高中举人,堪称少年得志。与其他清流不同,他曾历任南方要职,是少数兼具实务经验的言官。因其奏章直言敢谏,不惧权贵,赢得了铁笔御史的美誉。中法战争期间,他奉命参与勘界谈判,面对法国人的武力威胁,他坚守镇南关,最终不仅避免了割地赔款,还成功收回嘉隆河、八庄等失地。正是凭借这些实绩,他才能与张佩纶齐名,跻身清末四大名流之列。
对于征日之议,邓承修首先从国土面积对比入手:日本不过相当于中国两个行省大小。财政方面,日本国库白银储备从未超过五百万两,海军不足八千,军舰多已腐朽,武士总数仅四万余人。他认为日本之所以敢在朝鲜挑衅,不是不知中国实力,而是算准了中国不敢主动出击。
李鸿章对这两位清流的主张给出了经典回应:东征之事不必有,东征之志不可无。他清醒地认识到,自明治维新以来,日本全面学习西方,其首相伊藤博文亲赴欧洲考察,皇室成员留学俄国,其他使团分赴各国取经。西方之所以乐于传授,是因为他们与日本存在代差,且能从日本的发展中获利。因此每当中日冲突,列强总是表面调停,实则偏袒日本。
李鸿章直言:没有灭日实力却先露灭日意图是兵家大忌。他客观分析中日海军实力相当,远征日本并无必胜把握。但他同时强调,保持东征之志至关重要。最后,他回归现实,呼吁补足南北洋海军每年四百万两的军费欠款,认为只有建设强大海军,才能真正捍卫海疆。这番论述既浇灭了冒进主张,又指明了务实的发展方向,展现了这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。
发布于:天津市华林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